于是我转身,沿着苏醒的廊桥退向身后的休眠室。零碎的记忆里,像被加载了某种极高优先级的命令句,脚上的义肢承受着来自休眠室的引力。在此之前,我坚信自己是长眠又醒来的,某种不可抗拒的因素让我从四周充满绿植的室外苏醒,除了廊桥铁架下面氧化了的高密度材质机械臂,即便仓皇的向内收缩,也在这片高氧气浓度的空间里,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腐蚀着。
它们绝不该是这种情形,这种在我生活的时期刚刚成为新科技的“古早发明”,研究室对它们的习性实验的再详细不过,高抗氧化,是它成功的最大关键词。而同样的,我的那些日常不靠谱的、早就轮回了几代的同事们,他们的职业素养,也不会允许这样的破烂出现在如此伟大的计划中来。
我想:或许不止我一个人醒来。
这是一个荒谬但无法拒绝又细思极恐的念头,怀中的指南手册和记忆都告诉我这个计划的参与者——“我”,处在孤立无援的境地里。
一个尽管祷告上帝都只能单刷的BOSS级关卡,初始化的NPC非友即敌。
休眠室的门紧闭着,从里面,反锁的状态,平稳运行。
同我生活的纪元中那些科幻电影,对于非法苏醒后休眠室氧气外露、警铃大作、舱门损坏的描述大相径庭。我从来都不是能被幸运眷顾的人,能够见证这个同幻想背道而驰的科技。也正因如此,入选这个该死的计划,在那些“始作俑者”入土为安的今天,从未知的故乡醒来。
那个我意外苏醒的核心舱,倒是整个基地中最朴素的角落,单向透的磨砂玻璃让人从最开始就被注入一股探寻的恐惧感。我坚信,我坚信另一方向的空间里不会有同我对视的目光,作为一个空有百岁老人的自信心。
舱室的玻璃在我的抗议下换成了磨砂的,尽管同事们对于这样的改变会妨碍正常实验观察颇有微词,但还是执行了领导让他们关照可怜人的命令。
理智让我抗拒解锁那道门,回忆里,计划准备的后期我变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可怜人。原本促使我加入选拔的,我重病的父亲,在确定人选的三个月后依旧离世了。尽管我从言语和态度上都表示了对他们的理解,我的那些怀恨在心的同事们依旧在取消我的门锁权限后一并加上的电击回馈。
那个时候,后土的生存环境已经同那些科幻小说里面的消极幻想相差不多。我的父亲,一个过时的国营钢厂的普通工人,因为厂房中逸散有毒气体的,早已被钢灰烫到发黄的劣质吸氧管道,草草的在不到四十岁患上了有钱人八十岁的坏肺病——急性肺炎的一种。
好在的快速奔腾的科技事业留下了唯一的益处,无限过剩的生产力,于是大洋西边有了共产,东面的慈善事业更加癫狂。可惜的是,没有任何一款能够将人生平均化的机器,来回收父亲出生来的霉运。
更加难以接受的事情还在后面,人造的器官总是换上一个,就会连锁的一发不可收拾,但科学家们并不认为这是一件失败,而是归结于一个及其虚幻的名字“同化性”。
等待父亲仅剩的大脑即将被换成一套NAS改进的存储硬盘的时候,他的机械嘴巴表示了强烈的抗议,金属的上下颚磕的叮当作响。
我的父亲是一个奇怪的人,在没有因伤退休前,休息日,总会自己印许多画册,在这个机械永生的年代,宣传肉体长寿,甚至会坚持用自己的手指刷短视频,从而表现肉体的一点点作用。
父亲的主治医生是一个光头,他总乐意于站在模拟日光的下面同我们讲话。“又是一个拿光头当作学识渊博的蠢货。”站在母亲身后的我腹诽道。
他正在向母亲介绍一种新型的技术,人体胚胎。简单而言,就是将父亲的身体剥去机械义体暂时封存,等到他们的新发明生效,种出来一个一模一样的肉体父亲。作为交换,我需要在他们的研究单位工作不少于父亲重生的一半时间。
因为经过劳动局的精密计算,父亲的付出并不足以分配如此昂贵的劳动所得。
最近科研所来了一个光头的研究员,在我加入实验前的模糊记忆中,总会有相似的身影闪过,只是我从未忘记病重的父亲,以及苦苦等待的母亲,或许是个过路人,也未尝可知。
每天早上站在模拟日光灯下统计资料的时候总会晃到我的眼睛,磨砂玻璃的安装让他仿佛受到了奇耻大辱一样,即便看不到他的眼睛,我总能感觉到一双仇视。
就像现在一样,那种来自磨砂玻璃后的感觉。
那个光头除非是潜入的某种三头六臂的外星人卧底,我如此想的,否则碳基生命的寿命绝不会像仙侠剧中的那样长久。
我需要一个扳手拧开休眠室的安全阀门,跳过人工智能把守的刷卡门禁,于是它便在我脚边的废纸箱上安静的躺着,甚至连捡起的角度都恰如其分,只一行字迹顺着我抬起头的目光一闪而逝。
“安全阀的路是行不通的,他们将人工智能的底层逻辑篡改的一塌糊涂……”
字迹歪歪扭扭,像用手指某种蓝色生物积液涂抹上去的,后半段惨遭涂抹,浅蓝色的水渍在纯白舱壁上突兀且糟心。
安全阀的盖子是打开的,很轻易的,一圈两圈,来自舱室内的白色冷冻剂沿着松动的缝隙钻出,穿过带着电工手套的指缝,白霜攀附上身后的液氧瓶身。
警报灯亮了,那个一丝不苟的安全员将它设计的很大,在整个区域的正中心,但如今它也哑了,同我一样,找不到讲话和呼喊的理由,只那么突兀的闪烁,除了……
我确信那里也有一行文字,在上一轮警示灯照过安全阀旁边的时候。
“事件的发生和那里面的东西一样精巧,祝我和下一个我好运。”
我甚至不需要深究文字的含义,同我的如出一辙的字迹,工整的仿宋体一直都是学生时代鄙人的骄傲底气。
安全门的后面被一些东西堵住了,很严实,应当是那些比环境内新长出的枝干还要粗一些的电缆,门下的缝隙是刚好伸进手臂的宽度。舱内的冷冻剂凝成液体聚在门坎后,我想我找到提前苏醒的原因了。
“复仇!”手指上裸露在外的传感器被休眠室里面某条漏电的电缆输入了一些修复完整性的源代码。“我想这才是我的目的。”
紧随而来的,是一道晦涩且诡异的指令爬满全身……
“第23次苏醒体异常,启动销毁。”休眠室的培养仓中封存着一个人形智慧,或者可以说是,拥有除了灵魂之外其他全部生存机能的人类。舱内没有亮灯,微弱的监视器指示灯照在那人的光头上,微微亮的,像个应急照明灯。
笨拙的机械手臂从休眠仓中取下我仅剩的手臂。空荡的腹腔,轻巧的头颅以及23次的意外苏醒。
我想我应该向前走,作为一个刚刚苏醒的仅存人类,探索将是我内置的使命。
记忆跟来自不同个体拼接的高仿货一样混乱(第23次的意外终于浪费掉我的大脑),我想,休眠真是个奇妙的事情,起码比任何品种的生发药水都要管用。
只是,我需要抓紧将重生的好消息告诉我的好儿子。“一定要同那些资本家好好清算一下我熟睡的年份。”
那根老旧的器械臂终于砸向了下方的地面,可惜这次苏醒人工智能找不出为我装上耳朵的材料,同样的,如果传感器只能下一对的话,它应该被安置在仿制眼球的角膜后面。
穿过廊桥,走向存放着我的躯体的休眠室,我想我大概是可以用身份信息解锁大门的,只有那个被“天命”选中的、一文不值的讨厌鬼才会用撬开安全阀那样蠢笨的方法。(即便我确定应该为他取消验证的电击回馈)
可这是个笑话不是么,人们耗费成麻袋的金钱到这个建筑和项目中来,只是为了向这个更宜居,不知道几个纪元以后的世界送来一副义体、一个死人、几块器官还有早已叛变的光头博士。
这不应该是我的错误,我只是一个希望同我可怜的儿子团聚的,同样可怜的父亲。“该死的,这群**一定是二次利用了什么脏东西,还要跟别人抢脑袋,可惜我还没达到金丹的修为,不然肯定能祛除邪祟……”
“他不应该怀疑手册的准确性,作为之后22次意外苏醒的智商集合,他应该去开启那个该死的大门才对。只要那样,人工智能的指令就能完成、失效,销毁我可怜的灵魂。”可怜他的那些复制品煞有介事的写了“警示标语”。
舱门开启,冷冻液在流出的一瞬再次散成烟雾挂在那些可怜的树上,聋哑的人工智能什么都做不到了(它方才失去了仅存的一对传感器,献给人类的希望),“我”终于扛起自己的遗体,从培养仓中。
基地的大门在两纪元后的3850年再度开启,人们曾经将这扇门的启动定为人类下个时代的初纪元开端。仅剩尚且工作的终端开始通电,不远的岔路上,两株看不到冠的榕树架着一台显示器。
“欢迎回家,光顾新纪元的古人。”
“外来人员,物种检测”显示器边上加装了一个不易发现的扫描仪。
不多时,来自三面城镇的机器警察包围了研究所的门前,他们端详着光头博士的尸体。为首的机器人警官似乎热衷于摆弄自己的大背头假发,不经意的抹去了,一道蓝色的人造血液蜿蜒向身侧的密林。
“再次欢迎你的到来,亲爱的朋友。”警局的最深处,一个穿着钢厂工装蒙着人造皮的神秘人,向着现场照片的一角问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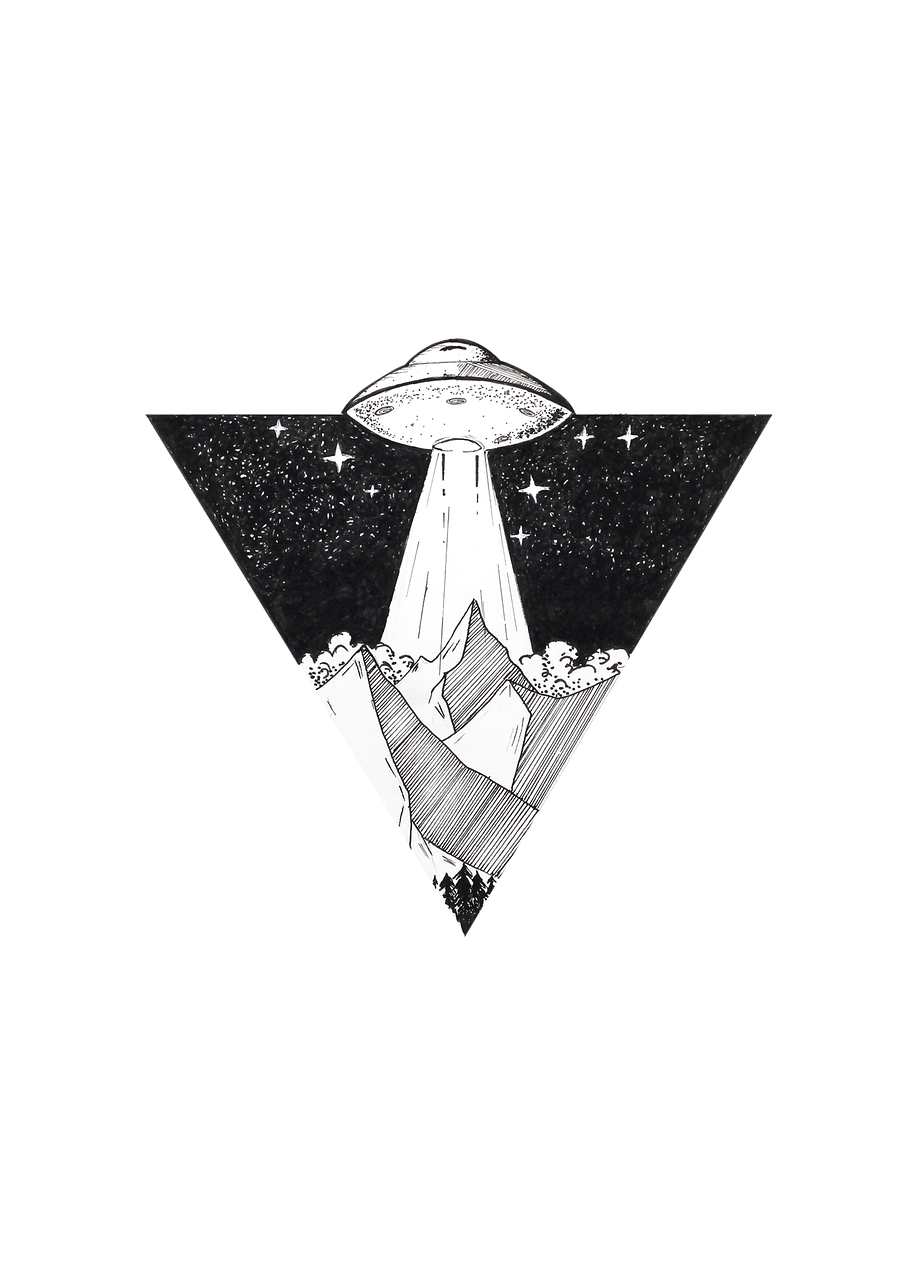
评论
发表评论